来自国内外各个机构的环境研究学者、经济学家开始考虑大气污染及其治理对中国经济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过去几十年内,他们苦心计算空气污染账是为了影响决策,在雾霾日趋严峻的现状下,他们也迎来了更为复杂的挑战。
一元钱投入换来多大的GDP增长?
大气污染治理中每投入1元,对经济将造成怎样的影响?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王金南给出的答案是:1元的投入带来1.12元的GDP增长。
据南方周记者了解,这个来自环保系统内部的测算为2013年9月颁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提供了重要参考。
据环境规划院参与此项测算的秦昌波博士介绍,环保投入拉动的不仅仅是环保产业,而且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的产值增长。当然测算仅仅局限于环保投入对环保产业及相关产业链的贡献,其他政策例如标准的加严所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企业能效提高等效益,规划院尚未计算。
事实上,在2013年《计划》的颁布前后,来自各个“智库”的环境研究学者、经济学家开始考虑大气污染及其治理对经济将造成怎样的影响。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搜索“雾霾”和“经济”,共计453条结果,这些期刊文章和报刊评论绝大部分发表于2013年。
最新的研究来自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张世秋教授领衔的课题组。针对2013年1月雾霾事件,课题组估算了因雾霾对交通和健康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230亿元。
另外一股研究力量来自经济学家。
2013年,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建立了定量模型,模拟行业政策与公共政策对PM2.5影响。在《政策要大变,才能将PM2.5降到30》的报告中,马骏指出,如果目前的煤炭、汽车、资源税、环保税费、公共交通政策不改变,将无法达到2030年全国城市平均PM2.5降到30微克/立方米的目标。
而四位来自中国、美国和以色列的经济学家则发表了燃煤取暖会减少寿命的论文。虽然没论文有提及经济损失,但是论文作者之一的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李宏斌教授在事后接受采访时做了简单的经济测算。
“大家都认钱,我们就计算成钱”
大气污染对经济影响的研究似乎开始成为“显学”,查询过往论文则会发现,在环境经济学领域,探寻大气污染和经济的关系的研究一直在进行。它们的专业说法是:大气污染造成的健康经济损失评估、虚拟治理成本、绿色GDP核算……
这些来自环保系统内的科研机构、地方环保局、社会科学院以及北大复旦等高校的研究者的结论主要告知环境污染损失占据GDP或GNP(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大家都认钱,那好,我们就计算成钱。”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易生说。
实际上,环保系统苦心算账是为了影响决策。
84岁的曲格平依然牢记三十多年前的一个数字:环境污染损失占工农业生产总值14%(当时尚未采用GDP概念),这个数字直接促使环境保护被列为中国基本国策。
上世纪80年代初,环境治理列入国民经济计划很难。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局工作的曲格平想找到一个有说服力的数字,即组织课题组计算环境污染损失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曲格平向主管国务院常务工作的万里副总理汇报了14%这个数字,万里很震惊,说要像计划生育一样,环境保护也应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借此大势,环境规划院原研究员过孝民成为了我国最早用模型计算环境污染损失的学者。郑易生也受时任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坤民的委托进行测算,一万块钱的资助,四个研究人员做了半年。
有意思的是,在国外,测算的结果往往表征对就业的影响,而在我国,为引起重视,测算结论都是一大笔资金,且要换算成GDP/GNP的百分比。过孝民的研究是1981-1985年间,平均每年损失为380亿元,占1983年GNP的6.75%。郑易生的结论是1993年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为1084.1亿元,占当年GNP的3%以上。
“这些数字造成的影响局限于学术界,对于决策界没有太多影响。”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说。当年夏光也测算过类似数据。
测算进入公众视野则是在2006年,原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家统计局首次联合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这是中国第一份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研究报告,也是国际上第一个以政府名义发布的绿色GDP核算研究报告。
可是,由于核算方法有待完善,纳入地方党政领导政绩考核体系还有待检验。绿色GDP的结果此后再也没有向公众发布,但环保部一直在继续计算,为内部决策提供参考。
领导担心“外国人抓住中国的把柄”
测算过程中,专家们一直面临数据、方法欠缺甚至领导层对结论不解的难题,直到PM2.5进入公众视野,这些拘谨才逐渐放开。
作为第一批研究者,参照国际经验,上世纪80年代,过孝民将环境污染的损失细分为对农作物影响、建筑物腐蚀和健康的影响,但方法存在很大局限性——对健康的影响只是对比了一个清洁的城市和污染严重的城市的发病率,饮食习惯等因素都无法排除。
此后,方法逐渐完善,常用的方法是人力资本法和支付意愿法。前者计算由于污染引起的过早死亡的成本,后者则是询问被调查者:你愿意为让你满意的空气支付多少钱?支付意愿法在国外应用较多,但在国内,“反正不掏自己的钱,被调查者的回答容易虚高。”郑易生说。所以中国大量研究都是基于人力资本法的计算。
国外机构的算法有时也很“滑稽”。1997年,世界银行《碧水蓝天:展望21世纪的中国环境》的报告指出,1995年我国大气与水污染的损失占当年GDP的比重高达8%,为历项研究中的最高值。参与该课题的郑易生记得,世界银行课题组的大气损失计算方法是由美国人寿保险的赔偿金除以50得来——因为当时中国人均GDP占美国的1/50,远远大于中国专家的计算结果。
另外一项2007年结题的世界银行资助项目的研究结论是,2003年有35.2万人因PM10过早死亡,由于中文版没有经过中方课题组校对就交到了环保总局,kill被直译为“杀死”,领导担心“外国人抓住中国的把柄”,就删掉了损失寿命,只留下损失金额。
其间,路透社和金融时报发现了报告的差异,称世界银行迫于压力,让数据缺席。这给中方专家过孝民带来了很大压力,他为此写了报告,解释早死的统计学意义。课题的研究结果只能在论文中发表。
同样参与过上述世界银行课题组的潘小川可能要幸运的多——过早死亡数据得以在新闻发布会上面世。当年风波结束5年后,2012年底,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潘小川和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计算了北京等四个城市的过早死亡和经济损失。虽然发布会后第二天,潘小川也接到了环保部的电话。
如今,大气污染致过早死亡已不再是敏感词。对于《计划》的影响,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的另一测算是:每年减少将近9万人的过早死亡。而在2013年底的医学界权威杂志《柳叶刀》上,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陈竺院士和王金南等合作的论文显示,中国每年因室外空气污染导致的早死人数在35万-50万人之间。
对大气污染的重视“不是数字推动的”
相比过往,环境经济学者似乎告别了宏观计算且大声疾呼的时代,但也迎来了更为复杂的挑战。
过孝民的学生们已不再纠结于宏观测算,而是回到具体的问题上。比如,环保部环境规划院成立了一个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计算例如河流污染的损失对人体健康、服务业、供水的影响,为事故赔偿、公益诉讼提供支撑。
“我们常用复杂性、长期性和综合性来形容大气污染问题。大家对这个词汇太熟了,反倒忽略了这些词汇背后揭示的真问题。”张世秋说,“我们需要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更需要科学研究、政策研究与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有效交流和沟通。”
郑易生已经退休十多年,很久没有关注大气污染领域的研究进展。看到满大街的口罩,他感慨当下对于大气污染的重视,是“人的健康推动的,而不是数字推动的”。
郑易生常对同行说,货币化很重要,但可以货币化的部分只是冰山一角。他参加的一个项目评审中,金额最高的一项居然是因为空气污染而导致洗车次数增加的钱,因为这一部分最好计算。
冰山之下的环境问题往往都是无法货币化的。“十年前我们计算各种数值,但喊半天不受重视。”郑易生说,“当时我们说要回到原本,也就是人体健康,才会引起重视,现在终于‘不幸’实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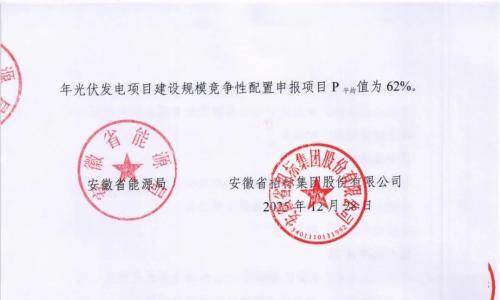





 扫一扫关注微信
扫一扫关注微信